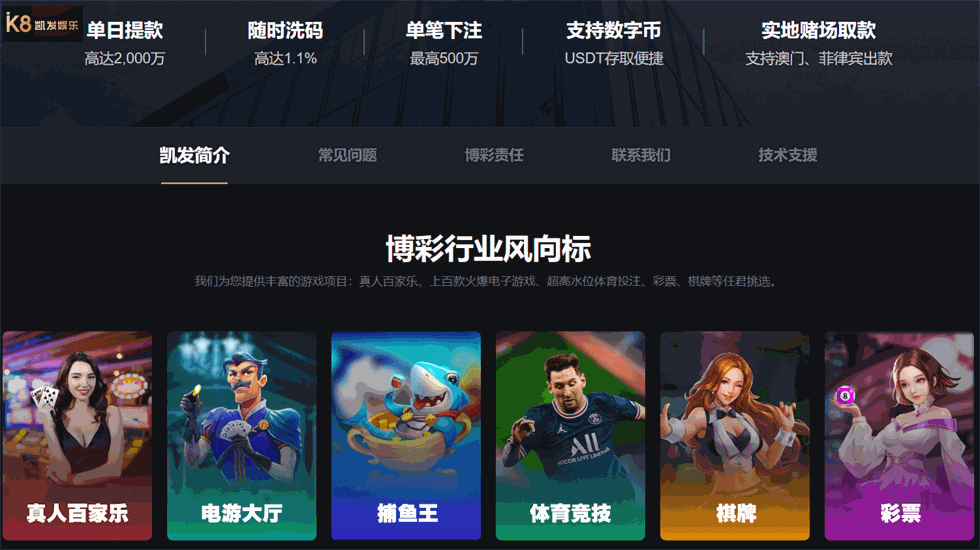-
孙毅安西影往事剧组趣闻录(之四)
发布日期:2022-03-03 14:19 点击次数:104
百有一用斋 08-09 15:48
原创 孙毅安 满天都是星
图片
摄制组是最热闹的地方,也是最无聊的地方。一般情况下,外景地都在异乡,人生地不熟,有戏拍的时候,各部门都开足马力,大家忙得不可开交,没戏拍的时候,比如下雨,又比如器材出了问题。像胶片没及时运到啊,导演突然病了啊等等意外发生,全组立刻就无事可做。
那么如此空闲的时光,大家做什么:赌博。赌博可以大张旗鼓,也可以因地制宜。手法也多种多样,最常见的就是打麻将,还有玩扑克牌,另外还有掷筛子的。不过通常还是以麻将扑克为主。麻将分北京麻将、西安麻将以及四川麻将。北京麻将的特点是点胡包庄,四人参与,谁点炮谁付钱。西安麻将也是四人玩推倒胡,一人点炮三人掏钱,最没有技术含量。四川麻将人数不限,可以四人也可以七八个人一起打,血战到底,谁点炮谁掏钱然后离场,赌注翻倍,最后两人决胜负,赢者通吃。输者损失惨重。不分出高低决不罢休,故而叫“血战到底”。扑克也有很多种玩法,红桃四、挖坑、福尔豪斯、砸金花或者叫飘三页。人数从三人到十几人,都可以参与。掷筛子或者比大小,或者猜单双。赌博是剧组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,也是导演、制片主任最痛恨的活动。一般都要瞒着导演、制片偷偷进行。但是如果导演、制片本身就是赌徒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每每这个时候,赌博在剧组就会大行其道,如火如荼。系列片《东陵大盗》的导演李云东自己就酷爱赌博,所以他的剧组,可以说是全民麻将。只要拍完戏,剧组感觉就是土狗版拉斯维加斯,每个房间都有赌博活动。经常一赌就是一夜,严重影响次日的拍摄。那时候,剧组还有临时党支部,于是支部书记就去和李云东导演谈,希望阻止剧组赌博。可是你跟一个赌徒谈禁赌,你还不如杀了他。李导演嘴上答应,坚决不改。书记说书记的,李导赌李导的,全组上下拍戏赌博两不误。支部书记忍无可忍,打长途电话向吴天明告状。吴天明倒是有些不以为然;狗日的不拍戏莫球事干,打麻将不算个啥。不然这伙子精力没处发泄给你胡整哩。书记在电话里快哭了,说:“厂长你不知道,这伙驴日滴一赌就是一夜。白天拍戏摄影端着摄影机都睡皮子咧。你再不管,戏拍不出来我不负责任。”这话把吴天明惹急了,别的可以不管,影响拍戏那可不成。电话里吴天明怒气冲冲低说:“你不管了,明天我一早坐飞机去天津!”书记放下电话就挺得意。回剧组碰见外联剧务。剧务说:“这天天打麻将,啥时候能拍完?”书记凑剧务耳朵边说:“狗日李云东打不成了,老吴明儿一早就来。老吴不让我给人说,你保密知道不?”剧务连连点头,转身就告诉了李云东,把书记给卖了。第二天,吴天明飞到天津,直奔剧组驻地。他不是一个人来的,还带了两个小跟班。到了驻地吴天明就喊:“挨个房间给我搜麻将!”招待所服务员逐一开门,小跟班们进去翻箱倒柜,把所有房间搜了一遍,一副麻将都没找到。书记傻眼了。吴天明说:“你狗日的谎报军情,连麻将都没有,李云东打个锤子麻将!”书记说;明明有,天天黑咧冷怂打哩厂长,我说一句瞎话我就是狗。吴天明摆摆手:“对咧对咧。你也不是个好怂。走,去现场!”吴天明到了现场,李云东正在拍大戏,现场几百个群众演员,都穿着国军服装挖慈禧太后的陵墓。剧务各部门精神抖擞,配合默契。李云东看见厂长来了,停下手里的活过来打招呼。吴天明摆手:“拍你的戏,少给我玩虚的。”晚上吃完饭,吴天明和李云东谈赌博的问题。李云东委屈得不行:“厂长我太冤枉了。我忙的哪有功夫打麻将?这都是哪个驴日下的和我有仇胡点炮哩。日了他妈的才在剧组打麻将!”吴天明:“你狗日也不是个好怂。明儿我回呀。厂里一堆事等我,你狗日敢打麻将叫我抓住,皮给你扒了!”第二天吴天明带着小跟班飞走了。制片主任一直送厂长到机场,看着吴天明进了登机栈桥,飞机一起飞就给李云东打电话:“导演,厂长走咧!”当天晚上,剧组开了五桌麻将,打得那叫一个爽。李云东正打得过瘾呢,门开了,厂党委马副书记走进来:“李云东,你胆大滴很,连老吴都敢骗!”原来,粗中有细的吴天明早看出蹊跷了:李云东是闻名全厂的赌徒,出外景不可能不打麻将。驻地搜出一两副麻将是情理之中的事,但是一副都没有,这里面绝对有猫腻。吴天明知道书记嘴上没把门的,肯定走漏风声了。于是不动声色,暗地里让小跟班去打长途电话,安排马书记立刻飞天津,但是天黑前不许到剧组,等李云东他们开始赌博,再抓现行。这个回马枪,端直戳李云东肺管子上了。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,开春创作大会上李云东做检讨的样子。他戴一副眼镜,手里拿着检讨书磕磕巴巴地念。吴天明用他独有的醋溜普通话骂他:“大声念,念麻利些!打麻将你劲大滴很么,这会儿不屁能咧?我看你是精钩子撵狼——胆大不要脸!”李云东皱着个苦瓜脸,台下哄堂大笑。
图片
1992年我的剧本《飞跃绝境》在宁夏拍摄,史晨风导演。他小名虎子,爷爷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开山导演史东山。按理他电影世家子弟,应该是文质彬彬,偏偏他长的就像个土匪,又偏爱赌博。我们在沙漠里都能想出赌博的办法。在《飞跃绝境》剧组,我创造了一个月不上床睡觉的历史记录。外景地在沙漠里,距离我们剧组驻地大约八十公里。每天要开车往返,最恐怖的是来回都要渡过黄河。而那时流经银川的黄河段,没有公路桥,所以剧组必须轮渡才能到达彼岸。这样,单程就需要两个半小时。往返需要五个多小时。我的剧组日常是这样的:早晨七点上车,立刻抢占大轿车最后一排当床睡觉,九点半十点到达现场开始工作。下午五点半收工,抢占后排睡觉,七点左右到驻地,吃完饭洗澡,开始打麻将,奋战一夜到早晨六点半,吃早餐上车继续睡觉……周而复始,天天如此。除了洗澡换衣服,我基本上不在自己房间待。剧组一半人都是如此。气的制片主任杨新在楼道骂大街:妈了个批!早知道你这一伙赌博轱辘子不睡觉,我把房钱都省了!偶尔打一场麻将,输赢靠运气。天天打麻将就没有运气了,技术好水平高的聪明人赢技术差水平低的二傻子。我是聪明人,可能智商比他们高吧,一个多月下来,剧组很多人的钱都到了我的口袋里。那些输得惨的,几乎身无分文。也有麻将打得好的。比如录音师旺旺,每天前半夜打麻将赢我们的钱,后半夜和虎子玩福尔豪斯,把钱输给虎子,然后改天虎子和我打麻将,又把钱输给我。天道轮回。不拍戏的时候,我们就去银川市区逛大街。那时候银川分新城和老城,我们开着车四处瞎溜达。前面说过了,走背运的家伙都身无分文,他们的钱,都厚厚地揣在我口袋里。所以逛街的时候,他们只得乖乖跟在我后面,我说吃什么,他们就只能吃什么,不想吃就饿肚子。走在大街上,他们事情还多,一会儿说:天气太热啦,来听冰可乐吧,一会儿又说:心情太差啦,买包烟抽吧。这种合理要求。我一般都会满足,但是他们有时候会提无理要求,比如有一天逛街。路边摊位上卖那种有很多口袋的马甲。俗称摄影背心。录音师延军坚决要求人人买一个。想得美。我根本不予理睬,结果几个家伙堵着路,不买背心不让我走。讨论很久最后达成协议:技术部门的赌徒,比如摄影、录音、照明,可以买一件,其他辅助性部门比如司机、剧务,就算了。管伙食的也想混件背心,被我严词拒绝:胡球扎势哩,整天买油买面买酱油醋,你要摄影背心挠球呀?打麻将虽好,最发愁的是半夜没烟抽。那时候没有24小时店,晚上过了八点基本买不到烟,更不要说二半夜了。虽然大家备货充足,可是架不住牌背心情差,这香烟消耗量就几何级数增长,对于烟鬼型赌徒来说,后半夜抽一根烟就是人间最美的享受。制片小春是个鸡贼。他每天半夜,都提前藏一根烟在窗户沿上,等快到黎明,大家都没烟抽了,他偷偷过去取出事先藏好的那支烟,美美抽一口,气的大家翻白眼,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。有一天,小春又在窗户沿藏了一根烟。我看到他鬼鬼祟祟的,没搭理他。趁大家不注意,我把那支烟偷走,给他换了一个脏兮兮的烟头。麻将打到后半夜,小春站起来伸伸懒腰:太乏咧活动一下子。说着他走到窗户旁,低头找着什么,然后就弯腰站着不动了。我问他:春,你弄啥咧?小春:莫事莫事。他还在低头查看什么。我说你跟个瓜皮一样,赶紧过来掷风!摇着脑袋走回来坐下,小春一脸迷惑不解的表情。我说你咋啦?小春欲言又止,半天说:莫事,打牌时间太长了,把我打昏了。这时我掏出一只烟,慢悠悠用打火机点着,惬意地喷云吐雾。小春眨巴眨巴眼睛:你烟阿达来滴?我使劲抽一口,把烟雾喷他脸上:跟你有个球关系。
图片
麻将在外景地打,回到家也打。剧组养成的习惯,一时半会改不了。有一次打麻将到了晚饭时间,大家派个人出去买肯德基,讨论说吃啥?
这个要汉堡,那个要鸡翅,东娃是采购员,说,圣代谁要?有人要有人不要?老孔跳起来说,啥叫圣代?给我也来一个!东娃说:你牙不好,圣代你咬不动。老孔:硬啊咬不动?不要了。平常不管什么,老孔就没有不要的。比如飘三页时谁开玩笑,说一句:咦,谁掉了一百块钱?虽然坐的位置距离很远,老孔拿着牌头也不抬:我的,我的!所以赌场采购员东娃故意这样说逗他玩。等圣代买回来,老孔火了:妈的什么狗屁圣代,冰淇淋嘛,谁说我咬不动?赌博已经成了西影人的文化之一。有时候,打一场麻将的时间之悠久漫长,令人无法想象。大约1996年某一天,化妆师小刚喊我:颜导家打麻将走,去不去?去就去,谁怕谁,左不过花点时间收你们的钱。于是我就跟着小刚到颜导家,开始垒长城。晚上十来点钟,打麻将的四个人,观敌瞭阵的七八个人。我因为第二天一早飞北京,就不玩了回家休息。我刚起身,立刻就有人补了我的空缺。第二天我飞去北京,到电影局听取对剧本的意见,然后回母校探望留校的同学,四天后飞上海。上海工作结束后,我去青岛,那里有一个剧组在拍电视剧。留连一段时间,我又回到北京,和导演一起工作,顺便参与演员的选定事宜。等这一切都结束回到西影,一个月过去了。第二天我去单位,向厂领导汇报我这个月的工作。回到院子看见服装师小文,他问我:颜导家打麻将去不?正打着呢缺个腿子。去就去谁怕谁?到了颜导家,几个人一边打牌一边说闲话。我问,摊子啥时候支的?新年一边揭牌一边说:“啥时候支的摊子,就是你出差走的时候。”我说你再不要胡交代了。我出差走了一个月。新年说走一个月咋?你走了麻将就不打了?摊子从那天就一直没散。笑死我了。敢情我走后,各路腿子天天跑颜导家打卡。铁打的摊子流水的腿子,居然了一个月换了几十个人,摊子就跟上甘岭阵地一样,一直都在我军手里。一个月过去,打海湾战争都打完了,颜导家的麻将摊子还在如火如荼战斗。这都不是最奇怪的,我遇到的最匪夷所思的事,是老姬的悲惨遭遇。老姬有一天手气特别冲。还没到半夜就一卷三,他把其中两个打得身无分文,行话叫:踢死了。剩下另一个在苦苦支撑。老姬想见好就收,于是提议算了吧,明天再打。老徐说:算啥?输家不开口,赢家不许走,规矩你都不懂了?老姬说你怂都踢死了,还不许走呢。打也行,现把现把把清。老徐一点没含糊:等着。我回家拿钱去,摊子不许散。起身开门走了。十几分钟后老徐回来,坐下付了之前所欠的赌债,继续接着打。天亮时,老姬被踢死了。院子里人声渐渐鼎沸。老姬灰头土脸精疲力尽回到家。老婆刚起床,看见他进门,甩了个脸色就进了卫生间。等她出来,老姬还在客厅坐着。老婆说:“你这人没意思滴很。”老姬:“我咋莫意思?”老婆:“打牌么。输了踢死了就回么,咋还让老徐跑屋里拿钱。”本来垂头丧气的老姬如同装了弹簧,一下跳了起来:“啥啥,你说啥?他昨天到咱家拿钱了?拿了多少?”老婆:“一万。他说你让来拿滴。”老姬:“你个瓜怂。我为啥不回来自己拿,让他来拿?你也不问清楚就给他钱?你得是脑子进水了?”老婆:“你才脑子进水了。老徐说你上厕所拌了一下,腿脚不利索怕上不了楼,所以让他来拿钱,你说我能咋办?我不给他钱你不是莫面子?”老姬气的在屋里跺脚。原来老徐被踢死后,竟然跑到老姬家拿了一万块钱做赌本,最终踢死了老姬。气的头皮发麻的老姬跑到老徐家兴师问罪。老徐不慌不忙。拿出一万块给老姬:“我向嫂子借的钱,如今还给你。好借好还,再借不难。”老姬拿着一万块。死的心思都有。只好悻悻回家。
图片
1997年,我很意外成为厂长助理。当了干部,而且是领导干部,当然不能赌博了。可是这些赌鬼绝对不会放过我。
有一天,我下午要主持一个创作漫谈会,正在办公室梳理自己的发言纲要,电话响了。是小春打来的。“小孙,老徐家打麻将!两点半!”我说滚蛋吧,我下午有会。就挂了电话,结果几秒钟后电话又响,是小刚打开的:“速度麻利,老徐家集合!”我一句话没说,挂了电话就去了会议室。整个会议期间,我的手机不停地震动,几十个电话不停地打进来。下午五点半,我结束了会议,穿过马路往西影家属院走,刚走到家属院门口,就看见小春、小刚、老徐、雁哥几个人排成一列纵队,向厂门口走开来。我心说这帮傻叉,在家属院走的跟巡逻队一样。小春走在队列前头,我说春不是打牌嘛你们干吗去?小春轻轻摇摇头,继续往前走。我这才发现,在队列最后走着两个陌生男人——坏了,他们被警察抓了。我不禁暗自庆幸,幸亏我要主持会议,不然我也就会被抓。好玄啊,看来努力工作还是有好处的。出了院子到了马路边,陌生男人开始拦出租,两辆车把这几个不知道拉哪里去了。我望着出租远去,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据说,小春到了分局又闹出新的笑话。当时警察问他:“你是个干啥的?”小春说:“我是制片。”警察问什么是制片?小春说,就是一部电影的所有事情都归我管?比如说吧,我最近就在拍一部电视专题片《李鹏的少年时代》……警察拦住他:瓜耐球你还是个制片?来来来,我先给你制个片。警察说着拿起一张白纸,在上面写下“赌博犯”,又写下小春的名字,然后让他举在胸前,用拍立得给他拍照。相片很快显影,警察得意洋洋地说:你觉得我这个片制的咋样?小春:我觉得还可以。
其次,四川麻将规则中还有就是关于记分的规则,比如对平胡,大胡,小胡的规定都有所不同。建议大家在玩四川麻将的时候要先了解这些内容,否则在游戏的过程中很难赢得高分。四川麻将的记分并不复杂,关键要看自己胡牌的情况,以及做庄和花牌的多少,这些对于记分都有直接的影响。